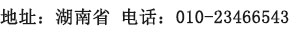故乡记事·三姓来源·我的祖上·之一·始祖
我的祖上——于家泡李氏一支,即吾乡所称“于家泡老李家”的始祖,大约于清代中晚期,由东距于家泡二十多里的本县长凝镇南城子村迁来。之所以说大约,是因为吾族虽曾修有族谱,对此有详细记载,但在年后,保有族谱,似乎成了一件可耻的事情,甚至因其为官方定义的、需要被清除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一种,有可能给家里带来灾难,亦或后人读书识字的少了,不能认知其价值,几乎所有家庭的族谱都已毁弃。到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族中最后一本由我的二爷偷偷藏于躺柜底下、布帘之后的族谱,也因地震时翻沙冒水彻底损毁。从此,这个家族的生活史,就没了文字记忆,只能靠我的祖、父辈中好古、好讲的人,或作为“瞎话儿”①讲说,或刻意讲传,使我们这些后人约略知道先世立足兴家的艰辛、宗族显赫的荣光和偶尔因对自身不能有所成就、愧对先祖的浅浅的自责、遗憾……
据老辈人讲,我的始祖是“一挑子挑着哥儿俩来的”,“一头挑着李丞,一头挑着李相”,来了就在村西搭一间草棚,落下了脚。始祖名讳为何?为什么迁离祖居?为什么只有始祖而无祖妣同来?这些都已不得而知。但始祖初来极度贫苦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给两位二世祖起名李丞、李相,李氏后人中有的非常讲究做人做事要“有横(土语读作hèng)劲”、“有血筋儿”②、有时甚至至于“混不吝”的程度,老人家应该是一位有志气、有脾气的人。
但是,不管你多么有志气、有脾气,作为于家泡的“外来户”,老李家还是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坐地户”老于家的压制甚至欺负。这由以下几事可以说明。
论“庄稼辈儿”,老于家的同龄人要长老李家一辈,老李家人见了老于家的人,叫爷、叫叔(土语读作shōu)的为绝大多数,而老于家人给老李家的人叫爷的几乎没有,叫叔的,则老李家人往往要比对方大十几、二十多岁;
远世无知,但自我这一辈向上推至我的祖辈,老于家的姑娘没有嫁到李家的,我的大姑、我的一位远房叔伯姐姐则先后嫁到了老于家;
于家泡有一口老井,在我的老太爷(曾祖父)一辈以前,老于家从不准老李家吃这口井里的清水,李氏一族只好绕远道从“西河”西南岸、属于梁泡村的一眼土井打水吃。光绪年间,滦河发大水,淹毁土井,老李家没了水吃,此时我的“大老太爷”已考中举人,只得依势到滦州衙门(时于家泡地属滦州普利屯)打官司,官府判定此井由两姓共用,老李家人才吃上了这口井里的水。
但于家泡李氏一族真是有“横劲”。先祖们有感、有恨于贫贱遭欺,既勤俭度日,积累财富、人丁,又下决心、出死力供后人读书,以求取“功名”,提高地位。到了第二三代,老李家已薄有田产,也有了财力供后人念书,先是“大老太爷”、乡里称为“润老爷”的——考中举人,下一辈又有人——李氏后人称为二老太爷、乡里称为“荣老爷”的——考取了进士,朝廷分发了河南知县,于家泡老李家终于成为当地的势族、望族,老李家人也才挺直腰板做起了人。
老辈人说,大老太爷、二老太爷考取了功名后,于家泡老李家一族曾多年在清明节回到南城子村祭祖,而每逢此时,二老太爷总是穿齐官服,走在长长队伍的前面。
大约、也许——族谱已失,也只能作此猜测——此时我们一族的始祖已经过世。如果老人家过世,他的在天之灵或许能够得到慰藉;而如果老人家在世,或许会长出一口休老之气吧?
而据《滦南县地名志》记,今滦南县(公元年由古滦州、滦县析出)长凝镇有南城子、北城子、北城子小庄、新城子、后场,此五村均为“明永乐初年,山东泰安县李岗寨人奉命迁至此地”③立村,则于家泡老李家的“老老家”,当远在山东了。
又有堪称奇事者,年夏天,我与几位朋友吃饭,席间有一位初次见面的小兄弟,不仅姓名与我一字不差,而且竟然是南城子人!于家泡老李家我这一辈以名字中的“洪”字排行,他们竟也是如此,而自中国被“新”之后,我们与城子村李氏,早已绝无来往。此或巧合耶?
但无论如何,我们相见,非常亲近。
——————————————
注:
①吾乡土语,故事,民间传说。
②吾乡土语,“有横劲”,能下狠心、拼死力做事;“有血筋儿”,有血性,立志坚定,能奋发做事。
③滦南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滦南县地名志》,第88-9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