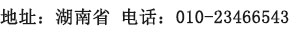故乡记事·少年玩儿事·挖“苗苗根儿”
年夏天,我考取滦南中学,成为一名住宿生,在学校住集体宿舍,吃食堂。刚开始的时候儿,吃食堂得换“粮关系”,就是每个月向县粮食局直属库交20多斤粒黍做粗粮、几斤麦子做细粮,直属库给开了票据,交到学校食堂,食堂按早午晚发给红蓝白三种饭票儿,才可以到食堂凭票儿打饭。我第一次换粮关系,是我爸爸着车子驮着我和粮食去的,粮食口袋拴在车子后衣架儿上,量小的细粮挂在里手儿,量大的粗粮挂在外手儿,我脸儿朝里坐在后衣架儿上。
我在学校吃饭,给家里带来了负担,不仅每个月要向粮局交粮食,尤其是交一定比例的麦子——上小学、初中在家儿吃饭,哪儿会月月儿吃面饭,一年又能吃几斤?而且一个月还得向食堂交7块钱,作为饭费,那年我二姐刚从滦南中学“下学”不久,我三哥21岁,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儿,我和五弟念书,正是件件儿事都得花钱的时候儿,一家子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儿花,我爸爸又是最老实纯粹的庄稼人,就指着在生产队挣工分儿过日子,上哪儿去抠这每个月必交的钱?但爸爸在驮着我换粮关系的道儿上却显得很欢喜,平时话很少的人,一道儿上和我拉了不少话,嘱咐我在学校儿听老师的话,好好儿学习。
在学校吃了几天食堂以后,我对学校的伙食非常满意。虽然食堂的粒黍面儿饽饽头儿撂冷了硬得象石头,秫米粥米粒儿硬得象枪砂——当时我们就把吃食堂的秫米粥叫“吃枪砂”,但一天三顿儿顿顿儿都能吃饱,晌豁还有一个炒菜,一碗用蒸饽饽头的“馏水”放的汤,这在家里,是想都想不到的好生活儿。
有的时候儿,就不免想到家里的吃食。在我们家儿,一年里除了麦收吃几顿白面,蒸一回馒头、烙一顿饼、切一顿汤,就是五月当午儿、八月十五、大年三十儿“一年三节”,也就是晌豁吃一顿秫米豆儿干饭,算改善了伙食,平时一天三顿饭,早下起来是秫米粥,晌豁是早下留出来的秫米僵巴粥,后晌或者再做秫米粥,或者着粒黍面儿做拔拉疙瘩汤,“盐精”是家里腌的白瓜子、黑瓜子(方言,白瓜子是盐腌的红萝卜,黑瓜子是酱缸里腌过,晒干的红萝卜),吃一顿萝卜缨子熬豆粒儿,或者熬一顿我们淘儿来的小鱼儿,一家人就欢喜得了不得。所以一年四季,我们这些孩子们最不爱过的就是冬天。春夏秋三季,田野、河沟里有无数可吃的东西,饿了可以随手摘、逮,可以生着吃,也可以烧熟、煮熟了吃,解饿、解馋。
一年里最早吃到的野生的吃食,是“苗苗根儿”。于家泡的“苗苗根儿”似乎只长在板儿桥西边儿、离板儿桥不远儿的板儿桥沟南沿儿那么一疙瘩儿。开春儿不大几天儿,这一段儿河沿儿冒出一种细绒戎儿却草叶儿直立向上、密密丛丛生长的小草儿的嫩芽儿,也知不道哪先起头儿,忽然有一天人们就聚到这儿,黑压压地一片,“人比草还多”。半大孩子拿着板儿锹,小孩子儿们拿着家里生炉子添煤的煤铲儿,争着抢着地占住地方儿,挖开草皮,拔拔拉拉地寻找“苗苗根儿”。庄里的孩子长到七、八岁儿,丫头小子就不一块儿玩儿了,除非学校组织活动,都是一堆儿一聚地各玩儿各的,但这时候儿却聚到一起,丫头们虽然不像小子生挖乱抢,却也不再忌讳,挤在人群里用心地挖地、寻找。
“苗苗根儿”比铅笔芯儿稍微粗点儿,多数儿有半根儿铅笔长,有的单根儿,有的象白薯根儿,几根儿攥在一起儿,细白脆嫩,嚼在嘴里有招人儿稀罕的新鲜甜味儿,很少渣子,小子们挖着了抖落抖落上头的土,当即放在嘴里嚼着吃,往往是挖一点儿吃一点儿,到最后回家的时候儿手里几乎剩不下啥,丫头们则着系头发的红绒绳儿或皮筋儿从当间儿系上,扎成小小的捆儿,拿回家洗了以后慢慢儿品尝。
“苗苗根儿”是啥草、菜的根儿呢?没人研究过,只是年年儿春天草芽儿冒出来的时候儿,人们就去挖。
吃过“苗苗根儿”,地里可吃的东西多起来,“屈末菜”“苦末菜”“秃老婆顶”“酸巴溜溜”……,孩子们不再挨饿,不用再象冬天一样饿急了四处儿踅踅摸摸儿地找吃的,大地,随时能用各样儿产出填饱他们的肚子。人们感恩大地,常说“大地母亲”,是的,这片平坦、广阔、丰润的土地,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