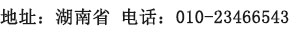尖角商时期(以下简称商)文化遗址位于昌黎县新集镇尖角村村西尖角小学院内。该校坐落于一沙丘高岗之上,其西南距崖上东沟约1公里,距滦河约2公里。尖角遗址是由昌黎县文物保管所石守仁、秦乃光、王明奎和新集文化站陈维民等人,于年11月29日在该校基建开槽现场发现的。12月4日至7日,笔者与所内石守仁、崔艳君、王明奎以及新集文化站陈维民、白正平等,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性的、抢救性的清理发掘,从而发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存。
一、发现的遗迹与遗物
这次发掘仅布东西长4米,南北宽3米的探方一个,方向正南北。所发现的唯一遗迹系位于探方中南部的一座灰坑。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其坑体未能全部显现。仅从发掘部分观测可知,坑口平面呈不规则形,距地表约cm,东西长轴cm,南北短轴cm,深65cm,其壁略斜,近平底。坑内堆积黑灰色,较致密。这次发掘共获得商文化遗物余件,其中完整陶拍1件,石器6件,其余均为各种陶片。遗物大部分出自灰坑,文化层中仅出土了60件陶片。陶拍呈月饼状,夹砂红褐陶质,直径9.5cm、厚2cm,两面和周边均饰以细绳纹,其中周边的细绳纹横坚相间,错落有致,陶拍两面均带有后来着意刻划的浅平沟槽。如此完美的制陶工具在冀东实为少见。大量的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与夹砂红陶为主,夹砂灰褐陶次之。胎质内红表黑的夹砂黑陶也较多,夹砂灰陶、泥质灰陶、泥质磨光黑陶均不多,泥质白陶极少,未见泥质红陶。陶器多为手制,兼有模制与轮制。器表多饰细绳纹,并有弦纹、方格纹、坑点纹等,素面与磨光者不多见。可辨器形主要有鬲、甗、罐、盆、瓮等,陶器有带耳、鋬者,较特殊者是1件磨光方形器。陶器中最多的是锥状足鬲,可见敛口卷沿圆唇、鼓腹者。有1件以陶片几乎复原起来的夹砂红褐陶盆(无底),其口径33.8cm。有1件夹砂灰褐陶敛口卷沿鼓腹鬲残片,知其口径10.8cm。石器共6件,可分砾石、打制和磨光石器三类。砾石石器2件,其中石砧1件、打磨器1件,均系以略大于手掌大的自然扁平砾石而用之,后者石质较粗糙,呈四边形,砺迹在相对之两边;打制石器2件,其中石英砂岩质砍砸器1件,小型黑色火成岩质刮割器1件。另有少量在打制石器过程中产生的断块、残片。磨制石器2件,皆为灰绿石质斧,其中有1件扁平双面穿孔石斧,其体长11.5cm、宽4.5cm、厚1.8cm,技术精良、造型美观,但刃部稍残,另1件石斧长13cm,横断面呈椭圆形,上略细,下稍粗,刃全残,并有重新打磨痕迹。
二、文化内涵与产生背景从陶器的质地,形式和纹饰与石器的形制和作风上看,尖角遗址的文化遗物,既含有燕山以北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又具有中原文化的一些特征。类似的遗址在昌黎邻县滦南东庄店和东八户以及唐山古冶等地已有发现,是地方性比较明显的一种青铜文化类型。由于发掘面积很有限,所以仅以出土的这些遗物来观察其原本整体文化面貌与特征,将势必由其局限性而导致认识上的偏颇与差误。但由于出土物较为丰富,其原本的一些主体文化要素还是能够显示出来:陶器质料以夹砂红褐陶与夹砂红陶为主,内红表黑的夹砂黑陶较多,细泥质磨光黑陶很少。泥质灰陶特别是泥质白陶更少;陶器多为手制,兼有模制与轮制;大部分器物饰细绳纹,多见锥状足鬲;见扁平穿孔石斧和少量打制石器。由上述可知,这里的陶器多为手制,以夹砂褐陶鬲、甗、罐、盆、瓮为主,器表以饰印绳纹为主。石器中存在着扁平穿孔石斧和少量打制石器。这些都是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同或相近之处。同时,这个遗址内涵的龙山文化因素也较多。例如,陶器中有较多的胎质内红表黑的夹砂黑陶和一定数量的细泥磨光黑陶,并有少量泥质白陶,最为多见的器物是锥状足鬲,器表多饰细绳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尖角的文化遗物虽然兼具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若干因素,但与二者又都存在差别。例如,尖角遗址不见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彩陶和细石器。尖角遗址中虽然存在素面、磨光的修饰方法,但其所占比例远远低于龙山文化。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尖角这一商文化的来源是复杂的。一方面有其地方性,即顽固地保持自身特征。另一方面是吸收其他文化因素。昌黎地处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历来是中原华夏民族和东北少数部族频繁交往的地区。尖角商文化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性,正是我国多民族频繁交往的反映,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和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三、面积与年代本次发掘的面积仅为12平方米,而且尚未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古钻探调查,所以尖角遗址的面积及遗址类型暂不能确定。但根据初步的局部的钻探结果和发现的遗迹与遗物综合分析推测,该遗址的面积应该是比较大的。首先,在这次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在探方南20米处进行了钻孔探测,结果表明在与发掘的商文化层深度相当的部位有与之类似的堆积物与包含物。这充分表明,至少发掘探方南20米处依然处于遗址的范围之内。其次,这次发现的灰坑,形体不规则,其内堆积呈灰黑色,且包含的陶片破碎混杂,并有些动物碎骨。据此,可以认定是当时人们倾倒垃圾之处。至于精致美观的石斧与完整的陶拍应为一时偶然丢失之物品,而并非有意抛弃之物。垃圾坑的存在至少表明附近有古人居住区。如若并非小群体临时居住之地,那么不远处还应分布着祭祀区和墓葬区等。再次,陶拍的存在昭示着这一带还应存在制陶区。但如果该坑仅为制陶人所用,那么遗址面积就会相应小一些。但不论哪种情况,所发掘的部分肯定是这处遗址的一小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尖角距滦南东庄店仅30公里,而且所具有的上述的文化特征在东庄店遗址中均能够充分地反映出来。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尖角遗址与东庄店遗址是同一年代、同一文化传统的古遗址。
年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了配合粮食部门基建,委由著名考古专家文启明先生对东店遗址进行发掘。在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灰坑和陶片、石器、残骨器及几颗青铜碎粒等商文化遗存。文启明先生在其《河北滦南县东庄店遗址调查》(载《考古》年9期)和《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载《考古与文物》年6期)两篇论著中均指出,东庄店遗址器物的形制作风,与唐山大城山、昌平雪山、邯郸间沟、磁县下潘汪庄等龙山文化的遗物殊为相近。而且文启明先生在后者中明确将东庄店遗址认定为“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中的早期类型”。文先生并进一步指出:“在时间上可能与山东龙山文化(14C测定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笔者注)的晚期相接近”。据此,我们将与东庄店距离相近,而且文化面貌相当的尖角遗址的年代也推断为早商是比较合适的。著名考古学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石永士先生在全面仔细地观察了出土标本后,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推定。所谓“早商”是指武汤于公元前年灭夏正式建立商朝,至公元前年盘庚迁殷这一时段。由此可知,尖角商文化遗址距今至少已有3千多年的历史了。
四、重要价值尖角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考古学、地方史志学的研究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现择其要者略述于下。
1.为冀东商文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份新的、珍贵的实物资料。长期以来,在冀东大地上发现的商文化遗址已达数十处。但经过科学发掘的地点却很少,所以,实物资料比较匮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考古学家对冀东的商文化的整体面貌特别是早晚期变化规律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而且对一些最基本问题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例如,许多学者将冀东这种内涵十分复杂的青铜文化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昌黎县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版)就采用了这一观点。然而有的学者却明确指出:“二者本不同源”。虽然百家争鸣是件大好事,但对问题长时期的莫衷一是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无庸讳言,尖角遗址对改变这种局面,虽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却为其得到最终的解决提供了一份新的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2.为建立秦皇岛地区的商文化考古序列和在本地区寻找“夏文化”,加助了强劲的动力。据文献记载,秦皇岛地区早年发现的商文化遗址有昌黎县的昌黎镇、邵埝坨、西张各庄,抚宁县的岭上村、荣庄、天马山、胡各庄,卢龙县的双望、沈庄、阚各庄等。从数量上看也不算很少。解放后考古学家们对冀东商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也作了许多,但主要集中在滦河以西的唐山地区。在综合研究中涉及滦河以东秦皇岛地区的只有卢龙阚各庄的商晚期的资料。自年5月唐、秦二市分治以后,秦皇岛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甚微。时至今日,商文化考古序列仍未初步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商时期文化的埋藏分布规律、发展演变过程、整体与阶段性的文化面貌、特征、内涵以及来源、交流等一系列问题,几乎全部是一笔糊涂账。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一个城市的魂。因此,这一落后现象与其著名的沿海开放旅游城市所应具有的文化品位极不相称。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尖角遗址的发现,使我市在已有的倍受方家吡美莫司乳膏关于北京白癜风的治疗